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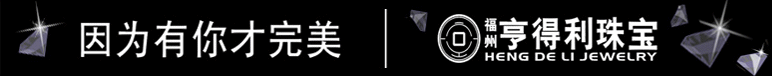
当67岁的陈世英走过香港那些挤挤挨挨的旧式房屋,仰头望去,看见熟悉的“走火通道”(消防通道),就会想起他的第一个工作室:在6层楼的“走火通道”上,那里放着他执业以来的全部家当:一台雕刻机,几把工具,两块石头。白天通道无人,他得以把工作台面支起来,晚上,这些家当就被收置进厨房。
那时候他不会想到,未来他会携带着他设计制作的价值2.3亿欧元的顶级珠宝出现在法国巴黎古董珠宝双年展上,并成为唯一一个多次受邀参加TEFAF(欧洲艺术博览会)的亚洲珠宝大师,不会想到他会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个华人珠宝雕刻家,不会想到他的个人作品集《梦光水》会获得美国印刷大奖最高荣誉班尼金奖( Benny Award),更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从珠宝设计跨界成为当代艺术家。他的大型雕塑个展《图腾》,此刻正在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建筑Fondaco Marcello中展出。
那个“可怕的中国人”什么都会
陈世英在国际珠宝舞台亮相频仍,提起他,老外有时会说,那个“可怕的中国人”。
高级定制珠宝是欧洲人的天下,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世界顶级的珠宝展会上,少有中国珠宝商的身影,连亚洲品牌亦不多见。有人好奇问陈世英,我们这里大多数珠宝品牌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你呢?陈世英说,我有五千年文明。
长期繁荣发展让欧洲珠宝工业有着严格的质量品控,和精细化的技术分工,外国人会问陈世英:你到底是抛光镶嵌师?还是宝石切割师?是设计师,还是雕刻师呢,“可怕的中国人”回答道:我什么都是。阴雕、阳雕、线雕、浮雕、内雕、镶嵌、润光……他几乎一个人吊打珠宝工业流水线上的所有工种。
什么都会,在一开始,只是生存的必须。刚刚自立门户的时候,他常常几个月都卖不出一件作品,有家公司找到他,问他:陈世英啊你识唔识雕cameo(浮雕宝石)啊?
在此之前,他学的都是单体圆雕,中国传统图式,观音或者关公,而且都是雕不透光材料,西洋cameo更是见都没见过,但为了吃饭,也硬着头皮接下来。“我说好吧,我会雕的。”领了松石材料回去,他便连夜练习,之前掌握的圆雕比例几乎失效,下刀的刀法也不同了,不断揣摩要如何改变,才能适应有限的厚度,最终实现浮雕的立体感。
“花了很长的时间,最终做出来了,这个老板非常开心,就开始出售,结果卖得非常好,几个月之后,突然间老板找我,他说你马上回来!当时我在澳门,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只好赶半夜3点钟的大船,开了三个多小时,清晨7点多返到香港,老板的店还没开门,就在那边等。9:30老板来了,一开门进去,我看见桌子上面,摆的都是我过去4个月卖掉的东西,统统被退回来了。我心里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压住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老板倒很客气,见他清晨赶来,忙让手下人去买猪扒包给他当早饭,还叫买瓶汽水给他喝。陈世英心中忐忑:都退货了,为什么还待我这么好?
等他吃喝完,老板笑眯眯地开了口,说藏家非常欣赏他的作品,这批东西回来,是专门请他在上面补刻一个签名。“听到这里,我的心才算安落了。”
最初的签名是中英文双语:陈世英、Wallace Chan。客户却跟他商量说,能不能不要签中文名,Wallace Chan也最好把Chan 这个姓氏拿掉。陈世英感到奇怪,中文名不签可以理解,毕竟出口海外,外国客人看不懂汉字,但为什么英文名里连Chan也不要呢?客户说,只签Wallace就好,因为Chan这个姓一看就很像中国人。
“可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啊!”
香港的第一夜睡在浴缸里
陈世英祖籍福建,5岁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和几个姐弟去往香港投奔亲戚,住在婆婆家。到了香港的第一夜,婆婆安排给陈世英的睡榻,是在走道上洗手间里的浴缸。“连块板都没有,就直接睡在洗澡盆里。”
颠沛流离的香港第一夜给陈世英留下了强烈印象,让他意识到,此处生存极为不易,必须学会随遇而安。
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找不到工作机会,也无法看到未来,一家人在困苦中勉力求生。陈世英从很小就要做一些零工来补贴家用,可能因为有一双巧手,打毛线、穿塑胶花,这些女孩子做的活计,他也做得很好。直到11岁,才有机会接受教育,父母找到一家没有正式牌照的学校,收费极廉,送他去读书认字。
“那个是五层楼高的天台小学,天台的楼下是一个菜市场,屋顶天台就是我们的学堂,学校用一块黑板隔开两个房间,两个班的同学同时上课,老师讲的话、黑板上面的写字,互相都能听到,隔壁在念书,我们也在念书的话,大家就都很吵,加上楼下小贩的叫卖声。那时我广东话也听不清楚,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写了什么,白蒙蒙一片,我以为其他同学都跟我一样看不清,不知道自己已经近视。我每天在学校发白日梦,没办法集中精神。”
读书之路走不通,16岁的时候,陈世英由叔叔做担保人,送到一家雕刻工坊里去当学徒。旧时手工师徒关系还延续着老传统,学徒工资微薄,不够吃穿,师父管午饭晚饭两餐,徒弟便也要在人身上依附于师父。二十多个师兄弟之间,是强烈的竞争关系,虎视眈眈互相提防,生怕谁偷学了本事,谁更得宠于师父。
“讲起来是学本事,但主要是学习怎么伺候师父,师父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打酱油、买菜、扫地、吃完饭后洗碗,师父出门,鞍前马后地陪侍……都是徒弟的分内事,几乎是个家丁。
有谁见过师父的刀法?
当时正是1973年,香港手工艺品行业乃至整个大的珠宝行业方兴未艾,陈世英投靠的雕刻作坊,主要制作象牙、珊瑚、青金石、孔雀石、玛瑙等半宝石材质的工艺品,除了供给本地的旺盛需求,还出口行销欧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主题也都是华人社会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观音菩萨、十八罗汉、百鸟朝阳、龙凤呈祥、牡丹孔雀,乃至各种雕花花瓶、鼻烟壶。
每天晚上8点下班,师兄弟们都走了,陈世英不走,他留在工作室里细看每个师兄弟的作品,研究他们的工艺。“白天是不能看的,他们会觉得我在偷师。晚上所有人走了,每个人的工作都放在台面上,我就不停地模仿,细看他们的工具,大家做同样一个东西,师父用的工具,跟师兄弟用的工具完全是两码事,我在两者之间推敲,师父用的是大刀阔斧,一刀就能到位,师兄弟做大件作品,却只能用很小的工具慢慢磨。我就去研究师父是怎么做的,每一刀怎么下刀,自己去做判断,师父是不会给我们看他的刀法的。”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似乎是每个传统手工行业的心结,师父不会倾囊相授,有心人只能自行学习。在从师的9个月里,陈世英感觉身为徒弟每天都在做重复的手工活。重复的好处,是锤炼了他们手上的判断力和准头,但长期原地踏步,沦为一个加工工具,却让他看不到出路。
严苛的竞争环境也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兄弟都很穷的状态下,吃饭就特别快,一餐饭,一分钟左右,他们已经吃完了,如果我吃慢一点,就没办法添饭。我吃饭本来慢,每一餐都吃不饱,我也只好飞快地吃,结果就熬出了胃病胃痛。”陈世英自小寄人篱下,习惯性勤劳,常常帮助煮饭的佣人洗碗擦桌,深得师父妈妈以及煮饭佣的喜欢,常常大家一样吃饭,他扒完白饭,发觉自己碗底埋伏着两块肉。这个秘密后来被师兄弟发现了,开始夹枪带棒地说些风言风语。“就说凭什么偏心你?你是不是拍马屁?或者你是不是喜欢老板的女儿,所以才这么用功?我那时候才十几岁,被他们说得我越来越难受。”他又强撑了两个月,最后坚决请辞,离开了师父。
开满白花的树下坐着孤独的贾宝玉
当时行业规矩,学徒三年学师、两年补师、一年谢师,一共要在师父门下服务六年才能离开,常常还需要押金,或者保人。“我只待了9个月就离开了,在那时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怎么会三年还没到就离开师父?师父肯定很生气,觉得自己丢脸。我父母更生气,我叔叔也跟着丢脸,他作为一个担保人会给人家说话的,我当时的状态,比一个小孩去念书,考试毕不了业更丢脸。”
只学了9个月,17岁的陈世英在走火通道自立门户,开始了自己的雕刻生涯。他央求父母给买了一台雕刻机,自己挖到两块石材,就开张了。大部分时间没有生意,他就步行四十分钟,到尖沙咀的橱窗外面去观摩别人的工艺是怎么做的,一边看一边用笔临摹图样,由于偷师的样子过于显著,很快就被人撵走了。
好不容易接到一单活,有家工厂交了一块青金石给他刻,“我很用功的,把所有的技能都在上面去做演绎,做了三个月,做好之后交给老板,心里很满足,觉得老板一定喜欢,结果老板一看,他说,你要表达什么?”陈世英百般解释,说这是一个花瓶,上面雕的是麻姑献寿,有松树,有仙鹤,象征长寿,但老板还是摇摇头把花瓶递还给他,说,就当我把材料送你了。
“他就是不要了。我们要吃饭的,三个月都没饭吃,也没有钱交给父母,当然心里难受,拿不到工时工钱,拿到这个材料有什么用?”
万般无奈的时候,他开始走街串巷兜售自己的作品,挨家挨户敲门,常常吃闭门羹。第一次卖出作品,还是偶遇一个卖欧珀(蛋白石)的老板,怜惜他年幼又勤奋,力逼着同行拿货,才做成的生意。
直到现在,陈世英还记得那件作品,是一尊圆雕的贾宝玉,衣袂飘飘,坐于石上,在一棵开满白花的树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题材十分罕见。“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些爱情主题,如果是做观音或者关公,可能很快就卖掉了。”
牙医钻头探入宝石的心
工艺锤炼人的智慧,石头的形状不规则,对于雕刻者来说,如果很粗鲁地把不要的部分切割掉,便是浪费了材料。拿到材料,工匠就需要不停地揣摩,跟石头去对话,根据石头本身的形状材质特点,因地制宜,把它最大化地、然而又是极自然地雕刻出来。
随机应变是石雕匠人的美德,“比方孔雀石、青金石,石头自然肌理有一圈一圈的纹路,这样的话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准备下刀的时候,要判断一刀下在哪里,这个材料会不会出现裂纹,或者本来是蓝色石头,但是一刀下去石头里面出现了白点,瑕疵,或者其他纹路,如果正好出现在观音脸上,买家就不容易接受。”陈世英说,雕刻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跟材料长期沟通的过程,“同时你得有两手三手四手的准备,一刀开进去,白点正好在观音脸上,我们就会把菩萨的头转动一点,或者脸庞弯一点,白点就没有了。如果还是避不开,我们就把材料转一边。如果这个裂纹继续走下去,没有办法定位,我们就把脸反过来,把背面做成正面。如果前后也没办法对调,我们就把作品做小一号。如果还是不行,甚至最后把石材整个翻转,上下颠倒过来。如果还是不行,连观音都得放弃,那么就看能不能改做八仙?八仙做不到,那么做关公?”陈世英说,材料改变,工匠的概念就得改变,工具也得改变,乃至创作者的个性都要随之改变。
陈世英喜欢看艺术展,从一切事物里寻找视觉灵感。在一次摄影展上,他被一幅多重曝光的摄影作品迷住了,忍不住琢磨是否用宝石也可以雕出多重曝光那种如梦似幻的光影。当时他已经不满足于浮雕宝石,开始研究“内雕”。所谓内雕,就是探入宝石内部去做雕刻,是非常精微的工艺。他研究了两年多,发现现有的雕刻工具难以满足他的需要,便决定自己研发改造工具,于是他去了一家机械工厂,再一次当学徒。
再一次当学徒,离他上回当学徒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香港的行业氛围发生了很大改变,徒弟不需要帮师父打酱油带孩子了,而他也不复是当时那个负气出走的少年。他圆熟地暗暗记下每个师父下午茶爱吃的点心,是冰奶茶菠萝油还是三明治,跑腿帮师父买来,请师父吃,闹烘烘的热带午后,师父们抽着烟吹着水,一点不费事就有点心吃,觉得这个小伙子懂事又勤力,他很快换来能动手上车床机械的特权。
陈世英目标明确,他认为牙医给人钻牙的钻头很好使,也许可以着手改制,作为宝石内雕的工具,但牙医钻头钻速太快,一分钟36000转,后来更快到一分钟240000转,高速转动带来的热力,宝石无法承受,常常只上一刀,宝石就裂开了。
陈世英说,材料改变,工匠的概念就得改变,工具也得改变,乃至创作者的个性都要随之改变
上帝和佛陀同时出手
因为沉迷工艺,陈世英个人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麻烦。他是那种不停发现技术难关、遇见问题就执着于解决问题的人,这种性格,当科学家合适,当个手工业者就意味着他总是要“做生”,不肯“做熟”。本来浮雕宝石卖得很好,他却不肯安安稳稳始终雕刻浮雕宝石,不肯做重复的事情,总要开发新的山头,而研究新工艺常常是几年的时光一把浪掷进去,却毫无产出。
“有一天,我在埋头雕刻的时候,突然电钻停了下来,怎么都恢复不了,我以为是工具机械坏了,就傻在那里,非常头疼。我已经没有钱再买工具去修理,我研究那个工具已经好几年了,只为了达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在雕刻桌前一坐下来就忘记了自己经济上的状态,我完全没想到,不是工具坏了,是电被拉了,我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他似乎听见屋外有人在敲他的铁门,他还呆呆地陷在自己的苦恼里,没去应门,但那个声音很执着,一直不停,他无奈地起身去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外国女孩子,手里拿着《圣经》,对他说:我们把爱带给你,把幸福带给你。
在陈世英的童年,他每天一早6点多钟会去教堂做早课,目的是仪式结束后能吃到免费而丰盛的早餐,只需要跟在人群中念叨45分钟,便可享用面包牛奶和水果。念完哈利路亚,吃饱了肚子,别的孩子去上学,没学可上的他跑回家,信佛的阿婆看见他回来了,唤他:世英,去上香,于是他也便跟着阿婆给佛菩萨上香,念阿弥陀佛。
两个传教的外国女孩唤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他回想起在他最饥饿的年纪,是在教堂里得过温饱,于是痛快答应参加礼拜六的青年聚会,因为那里会有饭吃。
在青年聚会上饱餐一顿之后,两个外国女孩努力用粤语发出他名字的发音,“她们说,陈—世—英,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难念的,我们给你取个英文名好不好?然后她们俩在那边叽里咕噜一阵商量,我也听不懂,商量完说,你叫Wallace好吗?你长得有点像我们美国一个将军,也像拉斯维加斯一个男歌星,这两个人名字都是Wallace,我说好啊,又能当将军又能当歌星,这名字不错哦。”
后来陈世英为佛光山设计制作佛骨舍利塔,塔的构建,需要理解佛教宇宙观中“三十三重天”的含义,他专门去请教,佛光山的朋友为了给他释义,翻出《大藏经》章节细解,却发现释迦牟尼佛生前不单是被称为“世尊”,也被称为“世英”,意为“世界的英雄”。“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原来连你的名字都在佛经里,怪不得你现在要来造佛塔啦,可能你前世就服侍过如来佛祖,给佛祖洗过脚的。”
中、英文两个名字都跟宗教有缘,冥冥之中,人生每次起落,也都有力量在照拂引领,当陈世英潜心研发的幻像内雕终于成功,取得专利,并在全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他将这道工艺命名为“Wallace Cut”,中文名“世英切割”。
以浅为深,皆为幻影
在拥有了牙医钻头改制成功的雕刻工具后,陈世英之前设想的在宝石上实现“多重曝光”逐渐成为可能。他尝试通过精密计算,在宝石的背面用360度阴雕的方式刻画图像,图像经过宝石不同剖面光线的折射,出现多重幻影。
始终难以解决的钻头过快导致宝石开裂的问题,在工具端解决不了,他就改变思路到工艺端去解决。他把宝石放进水下,手持机器伸进水里做微雕,让旋转产生的热能迅速被水流降低。
“但水下雕刻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水的波纹会干扰视线,你把一个筷子插进水里,水折射光线,都会让筷子变成不是直的。在这种状态下去雕刻,每雕一刀,就必须拿出来把水吹干,从不同角度再看,再放进水里小心翼翼雕一刀,再拿出来吹干……每一刀每一刀都是这样,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没有躯体,那一刻没有声音,也没有我的存在、也没有工具的存在,只有一块石头,跟我的心在互动。”
因为难度大、试错成本高,他先是在玻璃上反复练习,有了一定把握之后,再用天然水晶做试验,天然水晶的硬度跟海蓝宝、紫晶接近。等他终于胸有成竹的时候,他在海蓝宝石上面雕刻了一尊荷莱女神。
荷莱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掌四季轮替的女神,在通透的宝石上,光线在不同切面上折射,透出女神的一张正脸和四个不同侧影,但其实只有正面是雕出来的,其余四个,皆为幻影。女神高鼻深目的面部轮廓被反射后,微妙剔透,纤豪毕现,这种虚空中生妙有的雕刻法,也训练着雕刻人的逆向思维,因为肉眼在宝石中看到的最深处,其实在雕刻上是最浅的,而肉眼看到的左,在雕刻时其实是右,在创作的时候,一切思维都必须遵循逆向原则而行。
“但这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因为一件作品的成功,Wallace Cut的发明,把我带到国际上面,但事实上,我做出最成功作品的时候甚至过得比以往更穷,我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又非常奇妙的经历。”一般珠宝品牌的logo都隐藏在背面,但所有Wallace Cut的宝石,陈世英的签名都镌刻在正前方,一眼可见,因为那里不会产生折射,不会干扰光线,他也绝不会漏掉Wallace Chan里那个姓氏,Chan。
只买一粒宝石的神秘中国人
陈世英每次都从一个德国宝石商那里买材料,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德国人发来的电报,说要来香港,问能否拜会。没有工作室,陈世英就在自己老旧的住宅里接待了他。老外倒也毫不介意,只说对他好奇,别人买材料都是成批成批买,定期订货,只有这个神秘的中国买家,每次只买一粒宝石,买完就长久地失踪了。他问陈世英,到底你是做什么的呢?
陈世英拿出自己的幻像雕刻给他看,老外一看,大为惊讶,马上从包里掏出二十多块非常精美的、尺寸适合的宝石,一股脑地摊开,请陈世英挑选。“他说这是我收集了很久的,我就全部都给你,你一年后再付钱都可以。”
陈世英很尴尬,他每次只跟德国人买一块宝石,就是因为他只够买一块材料的钱,而且,按照Wallace Cut的精雕难度,可能一年时间也雕不出两块,自己是个只懂雕刻不懂销售的人,根本没钱付账。现在别人远道而来,又满腔热情,他不好意思,只得选了两块,德国人又硬往他手里多塞一块,并邀请他去参加在瑞士的展览。
德国宝石商人在瑞士展上拥有四个展位,他愿意分享一个展位给陈世英,但陈世英手头无钱无货,他只要了一个橱窗,橱窗里只放了一块Wallace Cut的宝石。
那是陈世英开眼看世界的一次机会,他根本待不住,天天跑去其他展馆偷师学艺,意大利馆德国馆法国馆,看钟表看珠宝看设计,眼神直直如带钩子。等他再回到自己展位,发现他的德国朋友特别开心,因为橱窗里那件“Wallace Cut”,这位德国宝石商人今年多接了好多订单,以前从来不看他展位的大品牌们,也纷纷跑来看这件作品不可思议的工艺。这让陈世英明白了一件事,永远要做最好的东西,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Wallace Cut”雕刻的“荷莱女神”1987年获得国际设计大奖。1992年,德国宝石博物馆为陈世英举办了个展,这也是亚洲人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他被德国媒体称为“亚洲雕刻天才”。
以万物为师
陈世英的人生逆袭,有点像他所钟情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先辈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多没接受过系统教育,只是自幼在学徒作坊,以某种职业技能为起点,让好奇心引领自己一路在工作中摸索学习,哪里有需求,哪里就生长出新的求知脉络。
这位天台小学都只读了两年的辍学孩童,如今拥有多项科技发明专利,包括钛金属在珠宝创作中的应用、“世英切割”、翡翠切割润光专利技术、石镶石工艺、灵感来自明代家具的珠宝“内格榫卯镶嵌法”、“真空妙有”、“世英陶瓷”等等,并且多次受邀在大英博物馆、哈佛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伦敦V&A博物馆、巴黎政治学院、佳士得美术学院等地发表演讲或讲学。
他的一系列发明,就是在不断探索工艺极限的过程中展开的。顶级定制珠宝往往尺寸较大,黄金、铂金等贵金属佩戴感受沉重,他便开始研发用超轻的钛金属制作珠宝。同样体积的钛,重量只有黄金的五分之一。但钛的融点高达1700多度,用什么材质的模具,才能承接1700多度的高温?黄金熔点950度、白银930度,以往珠宝制作用石墨材料来承接融化的金银,可是石墨到了1500度就软如豆腐,很快就化掉了。于是他又进一步研发耐高温的陶瓷材料,比钢硬度还高五倍的发明“世英陶瓷”就是这么来的。
“我研究一些新材料,牵涉到物理、化学、冶金很多科学经验,也会找一些其他行业的大佬请教,香港第一,台湾第一,包括伦敦、德国第一人,我都去找,但他们都觉得不可能,觉得我外行异想天开,甚至有点生气,觉得挑战了他的权威。最后我还是只能回到自己的世界,不停地实验,不停地反思,不停地去向材料本身提问。我没有老师,反而万事万物都是我的老师,然后它们又会变成我的同学。”
最后他找到解决方案,从把钛在固态转变为液态的时候,不让这个变化彻底完成,控制在90%的液化程度,此刻钛像水银珠一样可以灵活流动,又不会散开,恰好拿捏这个状态,把它注入含陶瓷成分的耐高温模具。
陈世英花了八年的时间研究钛,在珠宝行业内几乎无人理解,贵金属才有市场,谁会买钛做的珠宝?八年后,他在巴塞尔专场展示了自己的成果。而这一独特发明,也为他从珠宝设计跨界到大型钛金属当代雕塑领域奠定了技术基础。
钛是可以跟人类心脏一起跳动的金属
陈世英最早对钛金属发生兴趣,是因为一篇心脏起搏器的新闻报道。作为太空金属,钛在科技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也被认为是代表了未来的物质,但钛又是跟人类肉身最没有排斥的一个金属,无磁性、无毒,做成假牙或者心脏起搏器,进入人的身体两个月左右,就会跟人类的神经和肌肉连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钛是可以与人类共生的金属。
雕刻宝石的时候,得由硬度更高的钻石来完成切割雕刻工艺,雕塑钛的话,除了钻石,还需要用到钨钢。陈世英摸索出一整套制作大型钛雕塑的工艺,铸模完成之后,钛的表面会出现一层非常坚硬的氧化层,需要一边打磨一边雕,来实现表面的肌理。钛虽然是以神话中“Titans”(泰坦巨人)命名,但其实是一种非常敏感的材料,甚至需要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下去铸造,但完全真空的环境,操作者的手会爆裂,要摸索一个合理的比例,把惰性气体注进去……很多当代艺术家都由助手操劳雕塑,可陈世英更相信亲力亲为的手感,大量的实验器械,也让陈世英的工作室看起来不像典型的珠宝工坊或雕塑艺术家工作室,相反,它像一个科学怪咖的实验室,一个像古人一样留着长髯、穿着黑色唐装衬衣的怪杰就埋头在他的工作台前。
2021年,陈世英在威尼斯举办了大型钛金属雕塑展览《钛坦:物质与时空对话》,这也是他第一次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对他多年来在雕塑和大型装置上的探索做出梳理。小时候在香港,他家附近有一家茶餐厅冰室就叫威尼斯,长大之后,威尼斯更成为他的向往之地,只要条件允许,每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他都不会错过观摩的机会。在他的威尼斯个展上,他把代表过去的铁,和代表未来的钛并置在一起,形成充满张力的二元对立。
5000年前,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铁器,而钛被发现的历史才短短两百多年,铁热情、敏感,“铁会记住每一天的天气和温度,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滴一滴水在铁上面,几个小时之后铁就变化了。”而钛是一种接近永恒的金属。陈世英用锈迹斑斑的工字铁,跟钛铸造的巨大头颅组合,那些脸庞带着冥想式的悠远宁静,任由工具般冷硬的铁框,开出扭转空间的缺口。
2022年陈世英再一次回到威尼斯,跟威尼斯双年展同期,带来另一场大型特定场域装置展览《图腾》。展览特别呈现了一件装置作品,由陈世英的10米钛金属雕塑部件组成,此前,这件作品曾于上海021亮相,但在威尼斯15世纪建筑Fondaco Marcello中被重新拆分呈现。一旦拆解,雕塑作为统一形象的完整性便不复存在,象征着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和脆弱崩塌、亟待待重建的秩序。
在所有宗教中,找到最神性的那张脸
在陈世英的大型雕塑中,令人目光久久不能移开的就是那些人脸。钛的波光粼粼,呈现出脸庞上所有纤细的微表情。这些脸庞不辨雌雄,无问东西,也消弭了时间感,他们闭目不语,仿佛不谙世事的少年,也像洞察了一切的老僧。
陈世英说,他一开始做雕刻就是刻观音和佛像,后来雕Cameo,常见题材是基督和圣母,做Wallace Cut的时候,又大量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形象。什么样的脸庞能够最大程度体现神性,体现悲悯,体现温柔和慈祥?在东方的脸庞和西方的脸庞、男性的脸庞和女性的脸庞、少女的脸庞和老者的脸庞之间,也许存在着最大公约数。
“我觉得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就没有性别,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创造也没有分东方西方,我希望能创造神圣道,可以通天通地,无分天界、地界跟人界。”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尝试过一个多月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温水保持生命最基础的热能,在呼吸吐纳的极致感受中,他感受到空气中万千微尘中皆有无数生命,“感受到花开花谢都有感情,树叶黄了我会哭,花谢了我也哭。拿一个杯子,放一个器物,都要轻拿轻放,因为上面的细菌也是生命。每块石头都有呼吸,只是它们几百年为一呼,几百年为一吸。”
有位大藏家是他的伯乐,收藏了他雕刻的许多佛像,也成为他在佛学上的引路人。这位藏家离世之后,陈世英跑去他墓地上长久坐着,“我希望知道是不是有灵魂的存在,所以我跑到坟场去找人。如果没有灵魂,他待在地下干什么?如果有灵魂,他能不能上来跟我对话?”
陈世英甚少向外人道的是,2000年前后,在他的事业初上巅峰的时候,他出家当过几年和尚,出家之前还散尽家财,烧掉过往所有照片,斩断跟昨日的所有连接,连最心爱的工具都统统分送与人,因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老天爷还是又给他一个回来的机会。还俗回家路上,他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身无分文,连想雕刻都没有材料,看见路边散着一些修路遗弃的水泥方块,意识到万物皆有其用,便把水泥块搬回去做雕刻材料。
“出家修行那段时间让我越来越了解所有宗教,不单对佛教,包括道教、基督教、印度教,甚至我还去了解摩门教那些,发现本质都是相似的,如果我只活在一个宗教里面也是狭窄,我要超越对单一的一种宗教的认知,最后就是爱天,爱地,爱万物,爱人。我的肉身有限,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我创造的作品活得比我长,会成为我生命的载体,成为我存在过的证明,也成为我留给未来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