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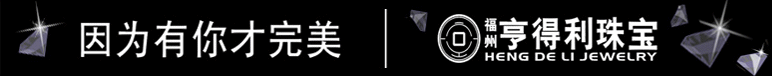
最近,在巴黎拍卖会上,一件宋元时期的哥窑锦葵形三足洗,拍出了149w美元(约合10,674,509rmb),满座皆惊。
惊的不只天价,还有背后的藏者——
Elsa Peretti,艾尔莎·佩雷蒂。

有多神?
《Vogue》将她形容为:珠宝领域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
不分男女,没有之一。

珠宝历史学家法塞尔更是惊叹得声嘶力竭:
“对我来说,她是珠宝界的先驱、开拓者,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
据《福布斯》统计,光是艾尔莎的设计,就占了蒂芙尼年净销售额的10%。
一骑绝尘的王者。

艾尔莎只用了15分钟,就拿下了蒂芙尼的offer。
1974年2月,没有相关经验,没有珠宝学历的她杀到蒂芙尼总部。
“艾尔莎坐在那里,穿着黑色斗篷,沉默而神秘。”
面试的高管回忆道。
她展示作品却遭到质疑:它们都由银制成。
在蒂芙尼高管看来,银代表着低级廉价,难登大雅之堂,不入珠宝门槛。
“我们都快25年没出过纯银饰品了!”

“用大颗宝石制作珠宝固然容易,但我更注重作品的舒适和美观。”
在墨镜投下的阴影中,艾尔莎的双唇冷冷地回击道。
“珠宝并非时尚。它必须经久耐用,而不是一有新东西就被丢弃。”

好大的口气!
但她的本事更大。
7个月后,蒂芙尼推出艾尔莎的首个系列,轰动全城,《Vogue》记者写到:
“从纽约到加州,只要有蒂芙尼专卖店的地方,就会排起长龙,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

艾尔莎的设计,没有万里挑一的稀世珍宝。
她推出89美元的碎钻项链,设计50美元的纯银花瓶吊坠。
“我为职业女性设计。”她笑道:“我想要的不是成为身份象征,而是以合理的价格呈现美。”
“女性可以给自己购买珠宝,不需要依靠阔气的糖爹。”

艾尔莎的作品,无需小心翼翼地供奉。
“我喜欢能够脱掉毛衣而不必摘下的珠宝。我喜欢能够戴着珠宝淋浴。”
“我希望珠宝不会成为累赘,它可以搭配礼服,也可以搭配衬衣。”
“自由,才是最矜贵之物。”
艾尔莎一夜爆火,名利双收,蒂芙尼奉上千万合同,顾客围得水泄不通。
“她为时尚界带来了最珍贵的珠宝:生命。”圈内更是赞不绝口。
然而就在这时,她“消失”了。
“每当我被困住,我就得跑,逃走。”
她生于保守的富豪之家,父亲拥有意大利赫赫有名的石油公司,母亲来自积厚流光的艺术家族。
但艾尔莎从小就是一个躁动的出逃者。

儿时,她与死神嬉戏。
“我经常和保姆一起去参观一座17世纪卡普齐纳教堂的墓地。母亲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送回去。禁忌之物会永远留在你身边。”她幽幽地笑。

少年,她与黑夜为伍。
“我15岁时就逃离家,在海边,就为了在凌晨一点跑去海边看海、看月亮。我一直在做那些事,一直,一直。”

21岁,她逃出那座镀金的牢笼,给家里写了一封独立生活的信,父亲立即停掉一切经济支持。
艾尔莎在学校教意大利语,在瑞士教别人滑雪,供自己读完了室内设计学位。
她这样描绘自己的人生:
“我认为我必须为自己而活……我现在必须自私一点来拯救自己。”
24岁那年,在友人的鼓励下她决定成为一名模特。
“一名注定不被喜欢的模特。”艾尔莎苦笑补充。
虽然拥有1.73cm的苗条身材,但她的风格和世俗审美格格不入。

短发背头,目光冷漠,性格刚烈。
她会因为老男人一句越界的调戏,当场砸碎一瓶威士忌作为反击。
也会因为一次事关原则的争吵,无情烧掉对方赠送的皮草大衣。
“你必须非常自信,但又不轻易妥协,这样才能成功。”
她方向明确,内心坚定。

就连设计珠宝的初衷,她都是为了自己。
在一次旅行中,盛开的栀子花让她神迷:
“呵护它垂死的灵魂,渴望让它永葆生机。”
于是,跳蚤市场上一个花瓶成为了灵感的来源——
经典的Bottle系列诞生了。

这种取法自然的理念,也成为了艾尔莎的作品最吸引人之处。
她钟情蔚蓝大海,于是画出了银质的海星。

有人曾送她一段可怖的蛇骨,她却看到了危险的美丽。

夜深时分,她曾因苦痛而哭泣。
于是她将泪水锻造成吊坠。
“愿脖子上有泪水,眼眶中就不会流泪。”

午夜梦回,她亦忆起那些童年被藏起的骨头。
于是艾尔莎描绘出了“Bone Cuff”。
如死神给手腕的婚戒。

因为太讨厌每次脱衣服都被首饰勾得纠缠不清。
于是艾尔莎以“线镶钻石”系列避开了容易勾挂的爪镶设计。

“我喜欢那些‘实用’的东西,比如那些一秒钟就能穿好的衣服和首饰,不用照镜子。
我几乎总是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因为对我来说,它们简洁、基本、优雅。”
“我是我自己的客户。”

最忠实的客户,是我自己。
最真挚的朋友,也是我自己。
艾尔莎就像亚热带的海风,有方向,不赶路,永远自由。

她和当时最时髦的摄影师 Helmut Newton谈恋爱,却从未走入婚姻。
只留下一张名垂时尚圈的照片。
“爱我,就记住最美的我。”
她的作品成了蒂芙尼的当家花旦,抢购的队伍比抢Labubu还疯狂,但她却选择了“离开”。
艾尔莎把赚到的所有钱,都拿去干了一件事:
修复古村落。

1968年,通过朋友一张照片,艾尔莎发现了圣马蒂老城。
那里一片废墟,夜里蝙蝠乱飞。
但好在山中有林,林下有海,风从岸边来,吹乱花海。

艾尔莎决定在此处隐居。
她保留村落原本的风貌,还原历史古老的颜色。

她将四处旅行搜罗的藏品放在老屋,用书籍和画作装点砖头和原木。


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不见富丽堂皇的摆设。
只有桌上一枝初采的梅花,在静静盛开。

“我的家有点原始,像一件旧毛衣。”
“冬天,我生火取暖,夏天,我泵水淋浴。”
打开窗,树影随风入梦来。

“我喜欢那些可以毫无顾忌地生长的植物,就像我在西班牙村子里种植的那些。
在那里,在那种简朴的氛围中,裹着套头衫,我梦想着、回忆着、想象着我将要设计的东西。”

艾尔莎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
她养了很多条小狗,还养了一头驴。


她一边给蒂芙尼设计新的产品,一边用赚到的钱购买村落的“危楼”,一一修复。
“当然,我创作很慢,”
她告诉《Vogue》:“我需要凝练形态,寻找本质。在工作中做到去芜存菁是一种持续的修炼,然后你也必须在生活中做到去芜存菁。”

她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和小狗、小驴、草木和鲜花生活在一起。
直到头发变白,年华老去。
晚年,艾尔莎依然佩戴着自己设计的饰品。
那是她最得意的杰作,也是她一部分的生命。

2020年5月1日,是艾尔莎80岁生日。
她写道:“能被大家以如此美好的方式铭记,我感到无比幸福。我感到自己又老又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星球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2021年3月,她在睡梦中离世。

山风吹入木窗,抚过那些古老的收藏和闪光的白银,仿佛再一次重复艾尔莎对人生的概括。
“我为自己而战,为自己而活。”
“一直一直。”